■滑溜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就在那个秋天,那个鲜花开满了农家小院的秋天,那个瓜果挂满了墙头的秋天,父亲在我的搀扶下,拄着那根崭新的拐杖,最后一次站在我老家的院子里,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娃娃, 无助地站在院子中央。
父亲的脸上努力的在挤着笑容。对,他就是这样努力的想笑。越是努力,给我们的感觉越是像哭。印戒细胞癌已经折磨的他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。头皮是蜡黄的,脸是蜡黄的,眼球也是蜡黄的。我像是在面对一个刚刚学会站立的孩子,搀扶着他又放开手,放开手要赶紧的去搀扶他。费了很大的周折,他才在院子里站稳了脚跟。明明知道我要给他照相,他开始努力地要摆出一个姿势。但并没有摆出来,只是在用无神的眼睛环顾院子的四周。他想摸摸那耷拉在架子上的长长的豆角,他想摘下那个嫩绿的爬在墙头上正冲他笑的丝瓜,他想抱抱那个懒洋洋的躲在南墙根里的胖冬瓜,他想去捡老母鸡咯哒咯哒下在窝里的蛋。
父亲似乎被定在了那里,双脚成了摆设。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,能够陪着我再度站在这个他已经站了几十年的院子,竟成为对我的最大奢侈。
父亲的竹子躺椅孤独地仰在院子里,上面尽管依旧铺着厚厚的棉垫片,但仍然可以依稀看到有厚厚的一层灰尘。父亲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再坐到这个躺椅上。因为他的屁股和后背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皮包着的骨头。而且那骨头格外的突出,几乎要蹭破了那层皮,露出头来。所以父亲不肯把屁股坐在那个躺椅上。甚至他怕把他的躺椅给扎破了。其实是他的骨头硌的他已经不能坐下。每坐一下都会觉得有人在用刀,要扒皮取他的骨头一样的疼痛。想让父亲坐下,其实应该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啊,可对于在平时这个有着锯灯泡子焊针鼻本事的我来说,已经到了穷途末路。我双手托着父亲的腋窝,好像捧着一块非常嫩的就要散架的豆腐。想轻轻的放都会把心提到嗓子眼儿。
不能坐着的父亲,只能躺在床上。躺在床上却觉得后背和肩膀硌得慌。我便去扶他起来仰在身后的被子上面。几分钟的时间就会又说屁股下面硌得慌。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,摸摸这里,扶扶那里,拽拽背角,掖掖被边,算是证明我在做着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,也算是给父亲做做孝顺的样子而已。
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官,为村子里许多家庭处理了数不清的鸡毛蒜皮的事儿,而且经常是我们一家人在吃饭或者讲将要睡觉的时候,那吵闹的人就会聚集到我的家里,让我的父亲去给他们评理儿。往往都是饭没吃成,觉没睡成,一顿你来我往的吵闹声就在我们家里上演。父亲讲完道理,数量半天这个,又数量半天那个,最后都以孝为先和为贵终结。百姓平安了,父亲的肚子里却装满了村民们的委屈和泪水。
法国著名诗人雨果说:“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,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” 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胸怀到底有多宽广,但从父亲能够把老百姓的苦水和泪水都能装在自己的心里,我可以断定父亲的胸怀已经跨越了海洋,超越了天空。
印戒细胞癌没有让父亲感到任何的疼痛,但是却让父亲骨瘦如柴。就在父亲坐着也疼痛难忍,躺下也疼痛难忍的这几天里,我第一次因为父亲生病请假陪在了父亲的身边。一直到临终前,他都无神地看着我,眼睛里一直汪满了泪水,絮絮叨叨地重复着:“大小,我当了一辈子村官,也没有给你们在城里买上楼,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存款,连个退休金也没有,就是个普通的农民……”
我蹲在父亲的床前,小心翼翼的附和着父亲:“爹,咱家很骄傲的,你是退伍军人,共产党员,我是人民教师,共产党员,您的孙子虽未毕业,却已经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,挽救了一个白血病人的生命……”
父亲说一次我就附和一次,我附和一次,父亲的泪水就止不住往外涌。我的泪水就会时不时的溅在父亲的脸上。
等到父亲再也说不出我也附和不上的时候,房间里便死一般沉默着,只有我们使劲相互牵着的手和我在使劲的上下左右的摇晃着的呼喊,唯独父亲眼里的那汪泪水还在热乎乎地打着旋儿。
父亲闭上眼睛的以后的很长时间,我都无法恢复正常。好像我的手还一直在拉着父亲的手。好像我能够把父亲从死亡中拉回来。
父亲,你到底在哪里?即使你在地狱,我也要再牵你的手。
(图片选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)
【编辑制作:滑溜,本名刘健。憨派文学创始人,著有憨派文学奠基之作《滑溜》一书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《中国憨派文学》主编。】
壹点号《中国憨派文学》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
X 关闭
财经排行
- 1、环球快讯:工信部:加快电力设备绿色低碳,发展高功率密度电机!
- 2、天天百事通!欧洲试图发展动力电池产业,却发现产业链掌控在中国手里
- 3、焦点信息:2022激光聚会活动回顾|ACS用于激光微加工的高性能运动控制系统
- 4、环球热推荐:丹佛斯服贸会携手三大国企,共创零碳未来
- 5、天天速递!精彩依旧,图尔克荣获2022CAIMRS两项大奖
- 6、环球速看:运用数字孪生+智能算法,行动元“末端振动抑制”技术超车欧美厂商
- 7、世界播报:锂电池快充或将突破技术难关
- 8、每日快讯!喜报!清能德创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称号
- 9、天天要闻:腾讯成国内首个获批创新医疗器械的互联网科技公司
- 10、环球消息!机器人的仿生之道
X 关闭
观点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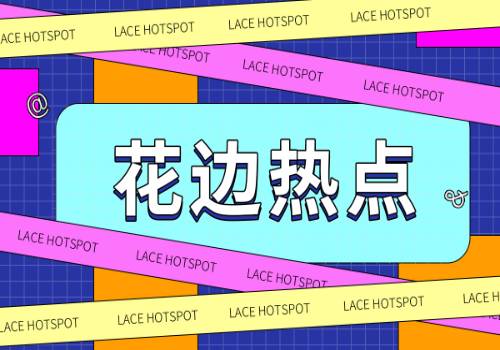
MINIElectricConvertible作为限量版敞篷MINIEV上市|世界头条
MINIElectricConvertible作为限量版敞篷MINIEV上市,具有固定规格和52,500英镑的价格标签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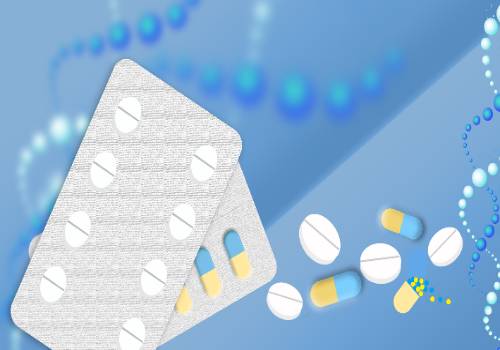
2023年4月11日苯胺动态-世界聚看点
纯苯:上周末买卖双方氛围寡淡,下午买方逢低入市,卖盘报价松动,低价成交好转。山东出货意向明显,报盘小幅下跌。预计今日早间华东纯苯震荡
-

德讯午评:大盘回撤 调仓换股
德讯午评盘面解析空头力量正在释放德讯证顾观点:大盘回撤调仓换股大盘震荡调整,三大指数小幅下跌。科创板跌幅最大,回撤空间或有进一步加大
-

全面注册制首日 10只新股大涨|予菲视点
昨日,A股主板注册制首批新股正式亮相,这也意味着注册制改革在资本市场全面落地。当天,10只新股平均涨幅达96 52%,其中涨幅最大的中电港收盘
-

伊拉克战争20周年丨美国的谎言从何而来? 精选
2001年,美国本土遭遇严重恐怖袭击,造成近3000人丧生。同一天,美国正式向恐怖主义宣战。美国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始于2001年9月11日时任美国总
-

浙江永强:4月10日融资买入734.49万元,融资融券余额2.38亿元-实时
4月10日,浙江永强(002489)融资买入734 49万元,融资偿还544 05万元,融资净买入190 44万元,融资余额2 34亿元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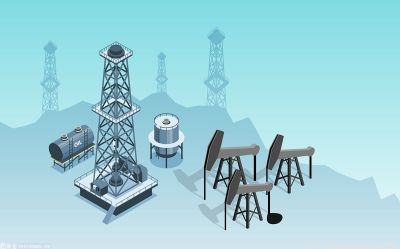
新股开板提醒:江盐集团打开一字涨停
快讯:江盐集团今日打开一字涨停,该股上市以来连续拉出1个一字涨停板。截止发稿时间,该股流通市值为22 50亿,中签后每股最高浮盈4 28元。江
-

景旺电子:4月10日融资买入841.26万元,融资融券余额1.57亿元 世界时快讯
4月10日,景旺电子(603228)融资买入841 26万元,融资偿还979 74万元,融资净卖出138 48万元,融资余额1 37亿元。
-

环球今日讯!小麦淀粉是澄粉吗(小麦淀粉)
1、小麦淀粉是从小麦中提取淀粉,过去是采用发酵法,即将小麦加水浸软、磨碎后,进行加酸发酵,使包围在淀粉颗粒周围的细胞被溶解而淀粉易于分
-

当前消息!香港复活节“小长假”游客忙 出入境旅游呈现双向复苏
当日22点左右,王晶晶一家五口从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大厅走出,她告诉中新社记者,这是疫情之后全家首次一起出游,总计消费在3万元港币左右,4天
